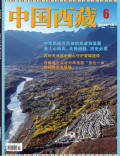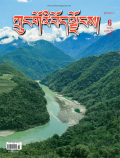孩提时,傍晚村落响起的“扎楞扎楞”之声,仿佛能唤醒他全身细胞,他放下手中的一切,飞奔着,向那令他亢奋的扎念琴声跑去;
小学时,他用一只不锈钢碗、一根废弃木头、用来包裹酥油的干牛肚皮、工地捡来的废弃工业线,自己做了一把扎念琴,如同宝贝般用到毕业;
中学时,他屡获“校园十佳歌手”称号,他弹扎念、表演、说唱折嘎,也写作,时常全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说,正是因为扎念琴,他的内心始终足够强大,富足,快乐。
他叫白玛次仁,因为传承、传唱、传播扎念琴这一古老的西藏乐器,从大学时,就在西藏以及四川、甘肃、青海等地涉藏州县小有名气。
而立之年,他以一位音乐教师的身份,用近乎痴迷的表演与教学方式,让更多学生从扎念琴艺术表演中,获得超乎想象的能量和自信。
这些年,白玛次仁像一位扎念琴的灵魂使者,将这一乐器广泛地传播给许多从未接触过乐器的人,让他们体验扎念琴的魅力。他将这一乐器从一个小地域的沉淀与传承,传播到更广大的区域。
源自地域的熏陶,扎念琴伴他成长
“上有快乐牧场,下有美丽田野,处在上下部间的鲁姆琼,是我可爱的家园。”
9岁时,还未上学的白玛次仁在叔叔的邀请下,为家乡口述了这首扎念琴歌词。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快乐的牧童。
白玛次仁的家乡叫鲁姆琼,位于西藏日喀则传统地理概念中“藏堆”昂仁县桑桑镇居藏村一个半农半牧的自然村落,全村只有12户人家。
长期以来,这一区域的人们在生活习俗上,既受到羌塘牧业文明的熏陶,也有后藏农耕文化的启迪。特别是相较于藏族传统扎念琴的几大流传地拉萨、工布、阿里等不同风格,流传于昂仁与拉孜的扎念琴风格以北派著称,与南派定日风格相对应,在“藏堆”地方,各领风骚。
生活在北派和上部阿里辐射地带的白玛次仁一家,就深受这一特殊区域的文化启蒙,他的爷爷石达次仁最爱讲英雄故事,格萨尔、松赞干布、米拉日巴、唐东杰布的传说,张口就来。他的一位叔叔布琼是当地人尽皆知的婚礼唱诵人,并且继承了高超的昂仁扎念琴弹唱技艺。
他们是当地文化名人,各自有过风光往事,白玛次仁的成长受他们影响极深。
由于身处农牧交接地域,鲁姆琼的村民在夏秋季节要赶着牛羊到草场更好的上部去游牧。白玛次仁至今记得放牧时的点滴往事,牛羊会跟着水草走走停停,他和叔叔布琼则随牛羊习性,紧跟一段,再歇一小会儿。
更多时候,叔叔会随手挎上他那把视若珍宝的扎念琴即兴弹奏一曲。那把用一头牛换来的好琴,一般人轻易碰不得。而小白玛则穿着藏装,腰间别上一把家人专门为他准备的“卡支”,那是一种专门在放牧时用来切肉的小刀。
他的骄傲和快乐是由衷的,因而从不觉得放牧是件苦差。“小孩配小刀,既有范儿又很帅。”回忆往事,白玛次仁忍不住笑出声来,那时的他只要去放牧,就能从叔叔那里学到很多关于扎念琴的传统技艺和歌舞。
在空旷的山野里,叔叔的扎念琴声随粗犷的风飘往远方,而小白玛则被叔叔的琴声打动,不自觉地站起身来,双手做出挎着一把琴弹奏的样子,欢快地唱啊、跳啊。
不同于其他季节,每到冬季,小村鲁姆琼会一下子热闹起来。夏秋时节远足的牛羊,此时可就近在休牧的冬草场入圈悠闲吃草,牧人不必再为追逐牛羊的脚步而远离家园。人们聚集一处,用扎念琴歌舞消磨寒冬腊月那枯寂的岁月。
那是白玛次仁最喜欢的季节。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他身着藏装,腰上别着“卡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来来来,让白玛来一段!”他似乎就在等待这样的一个召唤,他坦言自己从小就喜欢要“炫”一下的感觉。
每有机会,他总是即兴表演一番,或扎念、或折嘎、或说唱一段格萨尔,得到的不仅仅是大人口头上的赞美,还可能会有几块钱,甚至偶尔还有人奖励他一罐可乐。
“用扎念琴唱歌跳舞我最在行了。”这样的自信根植在白玛次仁的内心深处。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他是为扎念琴而生,也必将为扎念琴忙活这一辈子。
从乡土出发,扎念琴让他内心笃定
那年,爷爷对还无忧无虑的白玛次仁说:“你得去上学,我无法再将你留在家里了。”
2001年,得益于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规范与普及,爷爷石达次仁看重的第三代持家人白玛次仁在将满10岁时成为了一名小学生,这为他后来的人生开启了更多可能性。
白玛次仁在远离村落的桑桑镇上小学。3年级时,他用搜罗的各种材料自制了一把“劣质”的扎念琴,他拿着这把琴,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所有文艺活动,直至毕业,那把“七拼八凑”的扎念琴,才彻底被他玩坏。
由于白玛次仁成绩不错,6年级时,桑桑镇小学将他和其他两名有望考到其他省市西藏班的学生送到昂仁县小学,集中进入全县小考冲刺班。但他却因无法适应,几度逃课,最终成为了昂仁县的一名初中生。后来,他考到日喀则市一高时,那些和他一样来自日喀则西部县城中学的孩子,有些因为基础太差,学习跟不上而转学或回家的。
正是那些年,白玛次仁感觉自己像是“输在起跑线上”。高中时的他总是坐在教室后排,更多时候以沉默回应那种成绩落后的现实,经常独来独往。
但他依然放不下文艺,只要有机会就参加活动。每次活动结束,坐在前排的同学会转身指指后排的他,然后与同桌窃窃私语:“那个坐在后排的小子,好像他又拿了演讲第一名哦!”
而他在沉默中想得最多的仍是怎么把成绩赶上去。慢慢赶上去的成绩,以及后来一场场自创的文艺表演,渐渐打破他与其他同学的距离。
再后来,白玛次仁央求来日喀则市卖土特产的父亲,将原本用来买新衣服的钱,为他买了一把普通的扎念琴,他用这把琴在学校弹唱了一曲《阿克白玛》,从而一炮走红,从此,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喊他“阿克白玛”,直至现在。
高中时,老师问他理想的高校是哪里,他毫不犹豫地答西藏大学,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在那里自己可以继续学扎念琴。
高考前参加艺考时,他的音乐老师次罗把他带到西藏大学,结果他止步于第一关身高上,根本无法继续其他专业性面试。
次罗老师到处央求说这位学生才艺如何了得,引来多位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老师,给了白玛次仁一个展示才艺的机会,他用一段自己写的折嘎、传统昂仁扎念琴表演等,最终幸运地通过了艺考初试。
后来,他的高考成绩不错,有老师劝他报考其他省市更好的大学,他没有动摇,笃定地选择了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师范类专业。
大学时期,白玛次仁已经成长为校园文艺骨干。在老师的带领下,他有机会到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院校演出和交流。开阔的眼界,令他的思维和认知得以拓展,他和几位同届校友成立“雪莲花艺术团”,积极参加各项演出。
四年后,他被保送读研,成为西藏大学艺术学院主修扎念琴的研究生。他在心里默默念叨:“这并非我的人生终点。”
上研究生时,他和同学成立了“央萨扎念琴行”,这不仅能为自己挣生活费,也为社会上更多想学扎念琴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场所。
每逢寒署假期,白玛次仁总是背上背包,挎上扎念琴,前往定日、拉孜、昂仁和阿里等地的乡野山村,拜访民间艺人,了解更多关于西藏扎念琴的历史、传统和迥异的风格。他的硕士毕业论文《后藏南北扎念歌舞比较研究》,获得自治区级优秀论文称号。
研究生毕业后,白玛次仁如愿成为一名音乐教师。正如多年前一位藏文老师的教诲:以教师的身份,努力将藏族扎念琴音乐更广泛地传播给更多人,让藏族扎念琴声在弹拨间,传达快乐,也疗愈生活之苦。
融入创新思维,他用扎念琴普及快乐教育
2024年11月18日,高原寒冬已然临近。曲水县才纳乡境内的拉萨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晚自习刚结束,就有学生拿起扎念琴,跑到教学楼道的一个角落,卖力苦练起弹拨指法。
而在清晨6时,校园的食堂内,学生们早已各自找到位置,手拿课本或复习资料,为即将到来的艺考做力所能及的冲刺准备。
2023年12月,拉萨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个班的49名学生通过当年艺考,后又通过高考考到了相应的师专,成为他们曾经不敢奢望的大学生。
打破这所职高新历史的班级,正是白玛次仁到这所学校当上音乐老师后,所带领的首届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班。
4年前,当白玛次仁以一名硕士毕业生的身份踏入这所生源一般的职高起,他发现一些学生的身上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少孩子长期被家庭和社会漠视,普遍缺乏自信。
白玛次仁说,这些年,他试图用快乐教育法,改变孩子们性格中带有的自卑情绪。他用乐观精神,鼓励他们拿起扎念琴,至少从自娱自乐起,学着改变人生,改变心境。
他们中的多数人原本注定一生都将与扎念琴毫无关联,却很幸运地在这所西藏并不起眼的职高,遇到了白玛次仁。
白玛次仁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我的学生们最大特点就是心态好,他们不会无故自怨自怜,对遇到的各种恶意和挫折,能报以微笑,很多时候他们能潇洒地跨过那些沟沟坎坎,我认为这是我快乐教育法的一大成果。”
2024年11月2日下午,拉萨市纳金万达广场三楼的央喜书吧聚集了许多人。这天,白玛次仁带着他的十几名学生,在此上演了一场关于扎念琴的现场音乐课。
当天多数听讲者是带着家里的孩子来聆听的。家长们说,对白玛次仁其人早有耳闻,很感兴趣,也希望他的教育理念能让自己和孩子都受益。
不出意料,白玛次仁的感染力依然强劲,他诙谐幽默的口才,和与学生互动式的热烈表演,让在场所有观众掌声雷动,笑声不断。
他的学生们,一群来自拉萨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身着藏装,每人腰挎一把扎念琴,在随时回应老师话题的同时,可即兴来一场精彩的扎念琴表演。
“学音乐不能苦学,必须要快乐地学。”这是白玛次仁的教育理念。他的快乐教育法,似乎能让所有在场的人快乐起来。他在学校的课堂上,也会随时唱唱跳跳。
“我的教学中,学生们也是人手挎一把琴,我们是快乐的群体,我在我的快乐教育中获得许多灵感,这些是我和学生相互给予的。”他如是说。
白玛次仁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从小深受扎念琴音乐的熏陶以及家人的爱护,这使他内心笃定且拥有发现快乐的能力。
去年,白玛次仁的爷爷石达次仁在老家以93岁高龄离世。爷爷曾经说过的话,至今仍时常在他耳畔回响:“我相信白玛干什么都能成,去再远的地方也不会有事。”正是家人的信赖和放手,让他时常感到欣慰。
这些年,白玛次仁也时常回归故土。每到寒署假,他都会在老家村落举办公益教育,他教孩子们音乐、文化课还有普法知识,吸引了周边许多乡村的孩子参与,他希望这项公益事业至少要持续举办十年。
缘于自己曾受益于藏族传统文化口传心授方式的教育,后来又有幸接受正规的学院派和系统教育,白玛次仁渴望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慢慢将扎念琴教学规范化,他希望自己能编一些教材,如儿歌集以及兴趣爱好、考级、创作等扎念琴的曲目集,以及拉孜、昂仁风格和定日风格的曲目集等,“我要慢慢把这些都整理出来。”他说。
在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大力弘扬保护西藏文化的大好前景下,扎念琴的传统已有继承,且仍在持续,作为这一乐器的传承与教育者,白玛次仁对此感受极深。他说,在他的老家昂仁,年过30岁的男子几乎没有不会弹几首扎念琴的。这几年他走过西藏许多流传扎念琴的地方,在那里,弹一曲扎念琴往往是当地普通老百姓的节庆常态,也是人们排遣和抒发日常生活苦乐的一种方式。
现在,在三尺讲台和更广阔的舞台上,白玛次仁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与扎念琴的精彩人生。他常思考,在继承原有传统的基础上,如何能更好地将藏族扎念琴音乐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他认为,扎念琴还需要和世界上最流行的乐器接轨,要不断融入新内容,创新思维,以可持续的方式,在表演和演奏上,努力与时代接轨。为此,他将毕生努力,力争将这一传统乐器传播至世界每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