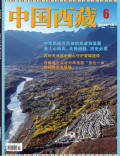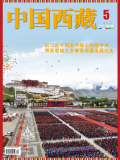文·图/章道珍 2014-11-27 15:20
在我记忆的长河中,曾有过许多的人和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都渐渐地淡忘了。唯独有一段经历,虽然被时间冲刷了近半个世纪,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每每回忆起来,总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深刻,一直鞭策着我走到今天。那是我们十八军文工团的文艺兵进军西藏的一段经历。

◎1953年拉萨龙王潭,章道珍(拉二胡者)和战友们在一起。
1951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十八军文工团正在为抢修甘孜机场的指战员演出,和着春风,无线电波传来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喜讯。为了执行协议,及早进军拉萨,我们立即开始了行军和进藏演出的各种准备。大家一面排练进军途中的鼓动节目,一面学习编排藏族歌舞。营房内外歌声阵阵,锣鼓喧天,一派欢乐和繁忙的景象。
出发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文工团根据需要,调整了人力。充实了戏剧、舞蹈、军乐三个区队的力量;事务长为我们领来了行军装备和驮运物资的骡马;炊事班增加了生活高原化的措施。为使我们习惯食用酥油、牛肉,增强体质,炊事班特意用米面、花生米和酥油熬出油茶,锅里煮着大块大块的牦牛肉,让大家各取所需。副政委郑旭同志像老妈妈照应孩子出远门那样,提醒我们正视征途上可能遇到的艰险,帮助我们精简个人行装。团长朱子铮也从难从严要求大家,对我们着装、搭帐篷、上驮子等行军演习中出现的一小点疏忽都不放过。
一路欢乐一路歌
我们文工团当时有一百五十多人,分别担负着戏剧、舞蹈、弦乐、管乐和舞台美术等任务,多数人只有二十岁左右,小的才十来岁,女兵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时的文工团是连队建制,区队相当于排,分队相当于班,而且大多数人是排以上干部。就是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每三个人才配备一匹骡马,用来驮运演出用的汽灯、幕布、服装和道具等杂物。我们不仅要步行,而且每人要背上背包、挎包、鞋子、水壶、米袋、两用篷布和筒装代食粉等,乐队的同志还要背管弦乐器,参加打腰鼓的同志要背腰鼓,大家的负重量都很大。
7月1日,我们和军直机关一道从甘孜出发了。一路上,人们不仅可以从我们扛的旗杆、背的腰鼓、乐器和人员组成上看出我们是文艺团体,而且还能从我们的情绪和作风上知道我们是文艺兵。部队从解放战争时期传下来的优良作风,在我们这儿得到了发扬光大:条件越差,我们就越注意调节自己的情绪,行军越艰苦,我们就越显得活跃。你听吧,在我们文工团的队伍里,不是这个区队在“拉歌”,就是那个分队在“碰球”,热烈的场面一浪高过一浪。善于说快板的大老肖(肖迎春)常常是大家“热闹”的对象,将他准备好的快板词都“掏”完了,大家仍不肯罢休,急得他只好一个劲地打竹板、挠头皮,无可奈何地宣布“哎,哎……,卖完了。”每逢爬雪山、涉冰河,大家都特别喜欢唱当时流行的歌曲:“谁是英雄汉?谁是软鸡蛋?不是吹牛腿,嗨!同志们战场见!”唱起这支歌,我们浑身就有了力量,两条腿也轻快多了,大步流星地跟着队伍。因为我们谁也不愿意落伍,谁也不愿意当“软鸡蛋”呀!就这样,我们一路走,一路唱,歌声不断;一边行,一边乐,笑声朗朗。由于行军途中的文娱活动开展得好,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都不觉得疲劳了。
在进军途中,我们文工团的同志不仅自己藐视困难,乐观豁达,而且处处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部队士气。部队前进到哪里,我们就紧紧跟随到哪里;战士什么时候想看演出,我们就想方设法地去满足。有时我们赶到部队的前面,放下行装后再走一段回头路,在部队将要经过的路上搭设临时鼓动棚,或在半山腰敲响欢快的锣鼓,给正在行军的部队鼓劲加油;有时我们在山顶上挥舞彩绸扭秧歌,慰问辛劳的战友;有时我们跟在战士身边,因人制宜地编上一段顺口溜。看到一个扛机枪的,就说:“这个同志不简单,扛着机枪登高山!”看到蹚着冰河过来的战士,又说:“苦不怕,累不怕,庆功会上戴红花!”我们的快板直说得战士们脸红心热,我们的锣鼓直敲得战士们脚下生风,雄纠纠气昂昂地迎着艰险前进。

◎1954年12月24日,在两条公路通车典礼主席台上。
到了昌都、丁青等比较大的城镇,我们还挑起汽灯、挂上幕布为藏胞演出,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各民族大团结。记得在丁青领粮时,有一群好奇的孩子围过来看我们这些女兵,我们就借机教他们唱歌。我们走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等歌声还在那里回荡。到拉萨后,我们在布达拉宫给达赖表演过大型秧歌剧《解放灯放光明》,这是我们团的保留节目,是我们进军华中南,在湖南与四野会师时编排的。我们从欢唱衡阳、邵阳解放享太平,演到贵阳、毕节、沪州、乐山、雅安、康定、甘孜、昌都、丁青解放享太平,最后演到拉萨解放享太平。一路上载歌载舞,好不热闹。我们给藏军各代本(团)唱过《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为迎接班禅由青海返藏,我们又赶排了促进前后藏两派之间团结的节目,那“回来吧!请快转回故乡,咱一同赶豺狼,一同保家乡……”的歌声,深深打动了爱国藏胞的心。
艰苦岁月战友情深
我们虽然是文艺兵,可我们的行军生活一直是紧张、艰苦而有序的。每到宿营地,各分队的同志都按照事先分工,分头卸驮子、放马、搭帐篷、砍柴、割草,各项工作井井有条,完全是一个团结友爱的战斗集体。大家知道,如果有一个人掉队,缺少他背的那块篷布,就搭不起帐篷。每个分队只有一只小帆布桶,我们洗脸洗脚、给马喂水都用它,谁也没有嫌过谁脏。临出发时,为了多背一点集体的东西,我们每人只带了一条薄被,睡觉时多是两人打通腿,垫一床盖一床。
夏日的高原气候多变。时而烈日当空,时而大雨倾盆;白天万里晴空,夜间大雪纷飞;山下绿草如茵,山上终年积雪。有一天夜晚,我们分队的马跑了,我和几个同志立即起身,分头在雪夜里寻找,直到天快亮时才找到。我重新钻进被窝时,被冻伤的脚痛得不能入睡,和我打通腿的高乐政把我的双脚搂在怀里焐,可直到起床也没能把我的脚暖热。待我跪着打好背包准备出发时,怎么也穿不上那双37 码的鞋,分队的同志找来了大老肖的42码鞋,我才勉强穿上。我在战友们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在队伍中行进。我的狼狈样很快就被军宣传部夏川部长看见了,他喊住我们团长问:“你们的人脚肿成这样了,怎么还叫她走路?”我们团长说:“她不肯骑马!”这时军政治部主任、七号首长刘振国牵着他骑的青灰骡子从我们队伍经过,不容分说,就把缰绳递给我,并和警卫员一起把我扶上骡背。骑在骡子背上,我脚上的疼痛虽然减轻了点,可让比自己年长一倍多的军首长走路,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暗自盘算着该怎么办。我向七号首长央求说:“越骑马,冻伤的脚血液越不流通,再这样骑下去,我的脚恐怕会坏死的。”首长听我说得真切有理,才接过缰绳向其他部队走去。
一天,部队行进到岗托,我和尹学仁等同志到金沙江边的一座山上割草,看到悬崖陡壁上的草因山羊也难吃到,长得特别好,就爬到悬崖上割。我们越割越多越舍不得走,连山头已被密云笼罩,大雨即将来临都没有察觉。大雨瓢泼而来,我们冒雨捆好草,坐在地上把绳子套上双肩,相互拉拽着才能站立起来。雨越下越大,我们背的草也越淋越重,到宿营地时,肩膀已被绳子勒出了道道血痕。回到帐篷,正在焦急等待我们归来的同志帮我们擦干头发,脱下湿透的衣服,还商量着怎样减轻我们次日的行军负重。

◎1949年11月,文工团铁腿班合影。
由于每天跋山涉水、淋雨踏雪,我们女兵的生物钟被打乱了,在进军途中大多不来月经,只在经期略感不适,但也有个别女兵月经照样来潮。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只能用粗硬的草纸铺垫,一段路走下来,大腿间被磨得血肉模糊,疼痛难忍,无奈间只好扯掉草纸,任凭经血顺着腿流。每逢要过较深的冰河,均由男同志先带绳涉水到对岸,在两岸间横拉绳索,再让我们女兵拉着绳索过河,免得被激流冲倒。尽管如此,每次涉过冰河,经寒风一吹,我的小腿肚上均要裂开许多血口,冒出粒粒血珠。
不倒的旗杆
从甘孜出发后,团部交下来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要我们把几十根四米来长的竹旗杆扛到拉萨,供部队到拉萨举行入城仪式时使用。戏剧区队的尹学仁身高肩宽,也和其他身体强壮的战友一样,义不容辞地扛了两根旗杆。
可离开岗托不久,尹学仁就病了。他脸色苍白,躬身弯背,走路也没过去那样精神了,但他仍然隐瞒着病情,坚持扛着旗杆。7 月17 日,部队要翻越达马拉山了,团首长号召大家发扬团结友爱精神,搞好互助活动,胜利翻过大山,进入重镇昌都。尹学仁也紧紧背包带和腰鼓带,扛上旗杆照常行进在队伍中间。开始上山了,他们分队又做起了“碰球”游戏。为了给尹学仁鼓劲,大家不时地找他“碰球”,尹学仁也尽快地把“球”碰给其他人。后来,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碰球”和输了“球”罚出节目的同志身上,不知不觉地爬到了半山腰。大家越爬越高,而尹学仁“碰球”的声音却越来越弱,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艰难地一步步向上攀登着。同志们都很关心尹学仁,分队长陈霁要接过他的旗杆,他不肯给,分队副肖迎春就抢下他的背包,凡走到能两个人并行的地段,其他同志也伸出手来,助他一臂之力,终于帮助他登上了山顶。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一过山顶,尹学仁虚弱得两腿不住地颤抖,该留步的地方留不住,该猛冲的地方冲不了,而且一口接一口地吐着淡红色的血水,再也跟不上队伍了。团里留下人和马照顾他,他仍然坚持要背着腰鼓扛着旗杆自己步行,他怕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就在到达昌都的当天夜里,年仅19岁的尹学仁同志带着满身风尘,悄然地与我们永别了。我们含着泪水,用尹学仁和同志们扛的旗杆,在昌都解放委员会门前的广场上挂起金黄色的幕布,搭起灵棚,给他穿上准备进拉萨时穿的呢子军服,悲痛地把他留在澜沧江畔。
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和评功选模后,8月28日我们扛起尹学仁扛过的旗杆继续向拉萨进发。过了丁青后,部队渐渐缺粮了,道路更加崎岖,大家的体质也明显下降。一天,军乐队的张国藩同志病得连马都骑不住了。在那连筷子丢了都找不到木棒代替的荒山雪岭,大家只好用旗杆临时绑了个担架,轮流抬着他走。舞蹈队的邓群阶同志也热心地去抬担架,没有人知道此刻他也在病中,为了帮助战友,他竟然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尽管如此,我们也没能挽留住张国藩的生命,就在那天晚上,他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我们搬开石块,掘开冻土,把好战友张国藩安葬在一座荒山下。
热心助人的邓群阶同志是在抬张国藩的路上倒下的。团里为了照顾邓群阶和其他几个病号,临时成立了一个护理班,我被指定当班长。护理班里有袁医助、葛若梁、管耀华和几位警卫营的战士。我们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线,缓缓地在后面跟着。我背着团里留给病号用的银元,牵着驮有药品和给养的瘦马,跑前跑后地照顾病号。天色晚了,我们在一个避风的河坎搭起帐篷,砍柴烧水做饭,然后给病号喂饭、喂药。邓群阶一直在不住地咳嗽,吐出的都是血水。夜深了,邓群阶的病情好像稳定了一些,我也疲劳地打起盹来。忽然,我被他抓挠衣被的声音惊醒,一转眼他又纹丝不动了。待袁医助赶过来诊断,邓群阶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眼睁睁地看着又一位战友离我们而去,我们不禁失声痛哭,我们向大地哭诉人民又失去了一位好儿子,我们告诉群山要永远记住这些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牺牲的战友。照着安葬尹学仁的样子,我们也给邓群阶穿上了呢子军服,用被子裹好他的遗体,在那条无名小河的岸边安葬了他。在护理病号的那段日子里,我时常躲着流眼泪,害怕自己完不成团里交给的任务,害怕再有生病的同志牺牲。因为那时候我毕竟只有17岁啊!

◎1952年8月1日在拉萨。
10月26日,部队胜利进抵拉萨。在举行隆重的入城式的时候,我们在队伍前面高举起40面彩旗,奏起了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打起整齐的腰鼓,行进在拉萨的街道上。我仰望着迎风招展的旗帜,好像又见到了尹学仁高大的身影;听着高亢的军乐声,好似又听到了张国藩吹奏的悠扬笛声;踏着胜利的鼓点,犹如又看见了邓群阶优美的舞姿。在这胜利的时刻,我们多么想念进军途中失去的战友啊!
我在西藏高原转战了半生,于1983年回到扬子江畔、紫金山麓,现在和儿孙们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想起进军西藏时的艰难险阻,回忆起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献出青春和生命的战友,我们应该更加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常常在心中默念:西藏——祝福你,我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