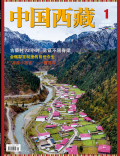新世纪来临的第二年,来自雪域高原的交响音乐已是第二次奏响在首都的音乐厅。
2001年9月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期间,曾由谭立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演出“雪域风情”——西藏交响作品音乐会。在那次音乐会上,新中国建国50年来第一次在首都舞台上出现了藏族作曲家创作的交响音乐作品。演出获得成功,作品也获得较高评价。
2002年3月14日在中山音乐堂成功举办的“西藏世纪交响音乐会”则给听众以更为深刻的印象,因为这台音乐会不但继续推出藏族作曲家的作品,而且演奏的绝大部分曲目都是作曲家为此次音乐会创作的新作品。听众对演出的热烈反应,是对此次音乐会和新作品最直接的肯定。
音乐会由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担任首演乐团。高伟春任音乐会的指挥。
为了使创作活动取得成果,推出优秀的音乐作品,早在2001年7月西藏举办“庆祝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盛大活动时,西藏世纪交响音乐会组委会就邀请了内地和西藏多位优秀的作曲家在西藏各地深入农村、牧区,了解西藏的历史文化,熟悉藏族人民的生活,学习各地丰富多采的传统音乐。作曲家先后访问了拉萨周围地区、藏北草原和东部工布地区。古老而庄严的喇嘛教寺院和海拔4700米的高原天池——纳木措湖畔,都留下了作曲家们的足迹。在深入基层生活的过程中,作曲家们亲身感受了藏族农牧民纯朴善良的性格、热情好客的习俗和劳动人民的生活风情。他们曾访问藏北那曲地区广阔的高原牧场,在牧区帐篷里,和牧民促膝谈心,品尝香气扑鼻的酥油茶,欣赏牧区热情奔放的“果卓”——圈舞和色彩绚丽的“拉鲁”——藏北牧歌。他们还访问过雅鲁藏布江畔的村庄,年老的船民们扛着笨重的牛皮船,为他们跳起粗犷厚实的牛皮船舞。在西藏东部墨竹工卡地方,有的作曲家还亲身体验了藏族神秘而圣洁的天葬仪式。这些实际的生活体验无疑给作曲家们以极其生动而深刻的印象,激活了他们的创作灵感。至今当作曲家们谈起在西藏的经历和见闻时,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西藏共包括一市——拉萨市,六个地区——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林芝地区、昌都地区、阿里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丰富多采、风格各异的传统艺术。借助于西藏50周年大庆的难得机遇,作曲家们得以欣赏到西藏各个地区民间艺术家集中在拉萨的表演,其中包括平时在拉萨也难得一见的,来自西藏最西部边陲阿里地区的音乐、舞蹈。这给作曲家们提供了比较全面地接触西藏传统音乐文化的极好机会。
3月14日北京终于迎来这场音乐会的成功演出。
此次音乐会上演的作品是:交响素描《洁》(旦增边洛作曲)、《涅》(杨勇作曲)、交响诗篇《雅鲁藏布》(张小夫作曲)、交响序曲《谛辩》(觉嘎作曲)、交响诗《遥望古格》(赵建民作曲)、音诗《雪域霞光》(郭文景、宝玉作曲)等六首。在节目单上还有两首作品《喜玛拉雅》(叶小纲作曲)、《纳木措》(韩勇作曲),目前尚未完成创作。
交响素描《洁》是西藏青年作曲家旦增边洛的作品。创作灵感来自于藏族古老的宗教信仰。作曲家意图通过音乐来体现藏族人民纯洁朴实的内心世界与美好的愿望。作品在藏族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借鉴现代作曲技法展开乐思,整个作品简洁、清晰,结构完整,音乐语言新颖但不怪诞,配器色彩层次丰富,民族乐器与管弦乐队结合自然。这首作品充分说明青年作曲家已较好地掌握传统与现代的作曲技巧,具有比较成熟的创作能力。《洁》在2001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时已经为首都音乐界所首肯,在音乐作品评选中脱颍而出,获得创作一等奖。
《涅》是我国旅美作曲家杨勇的作品。“涅”,在藏族民间传说中是雪山之神,它雄强威猛,住在高耸云端的雪峰之上,俯视牧场草原与芸芸众生。作品意图通过音乐以表现神奇的民间传说,并表达藏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音乐与古老的藏戏音调相连系,运用了大量现代作曲技法,强烈的节奏与音响体现作者对神话中的雪山之神的艺术想象。
交响序曲《谛辩》是另一位藏族青年作曲家觉嘎的作品。这首作品更多地具有探索与创新的意义,体现出作者在艺术创作上的追求。乐曲采用了作者的“模糊同构与复合体”原理精心构思。引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取自泛音列中的音高与时值、和声、对位、配器、曲式等置于‘模糊同构’的原理中,构筑了一部诸因素融为一体的‘复合体’。”聆听这首作品,显然是“现代”意味十分明显的作品,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作曲家并非在作品中单纯地作现代技法的探索,其创作意图是表达作者对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关注,对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追求,以及对开创西藏文化新辉煌的愿望;体现出藏族传统文化诞生、形成、吸收、成熟的艰巨过程。作曲家觉嘎曾在四川音乐学院接受过长时期的正规、系统的作曲训练,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少运用传统技法的创作。聆听者完全可以对作品《谛辩》作出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是青年作曲家创新的愿望也是应该得到理解的。
交响诗《遥望古格》是曾经长期在西藏工作过的作曲家赵建民的作品。这是一首颇有意境的乐曲。作品主要采用了传统作曲技法,音乐朴素含蓄。古格王国建立于公元10世纪,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古代的象雄地方)存在了近800年,曾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公元 17世纪时王国被拉达克入侵者覆灭。经兵燹后,几百年来,山岗、平野间杳无人烟,只留下古格宫廷和寺庙残存的遗迹。寂寞无语的断垣残壁,锈迹斑斑的弓箭、铠甲,颓毁的经堂,斑驳的壁画,古旧的佛像,……留任后人凭吊。交响诗《遥望古格》即诞生于作曲家遥念古格遗迹而生发的创作灵感,音乐充溢历史追忆的沧桑感和对藏族古代文明的深情赞颂。作品以西藏阿里地方的原始音调为基础,运用单主题进行变化、发展。音乐风格韵味浓郁。用藏族竖笛——林布(演出时以箫代替)演奏的古朴深情的旋律,前后呼应,其装饰奏法极有特色。
音诗《雪域霞光》是青年作曲家宝玉与他的导师、著名作曲家郭文景合作的作品。作曲家对此作品创作技法的定位是位于现代技法与传统技法之间,关注音乐的可听性。作曲家以 “雪域霞光”作为标题,“雪域”指西藏,“霞光”寓示西藏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作品以西藏传统音乐为素材,加以交响化处理,创造出三个不同调式的音乐主题,表示不同的内涵。白色主题以弦乐音色为主,它是人民的象征;红色主题运用了西藏古典音乐囊玛的材料,最初用圆号的音色,其后在其它木管乐器上出现,它象征着生命的力量;黑色主题以管乐合奏的音色为主,象征罪恶的旧势力。在奏鸣曲式的结构中,不同的、矛盾的主题经过、发展,逐渐转化、融合,在再现部的高潮中展现了白色主题与红色主题酣畅的歌唱,而黑色主题已经变形,节奏化,三个主题以复调形式交织,成为辉煌的颂歌。音乐最终希望传达给观众的感受是西藏光辉的未来。
作曲家宝玉是此次六首作品中惟一没有去过西藏的作者,但是从演出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依靠间接获得的材料与长期的知识积累,以及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也能使作曲家在未能实地体验的条件下,激发创作灵感,写出比较成功的作品。这种情况在中外音乐史上不乏先例。就以最近的实例而言,据笔者所知,作曲家张千一在写作歌曲《青藏高原》之前并未去过西藏,但是《青藏高原》已经成为许多藏族歌手的保留曲目,在广大藏区受到群众欢迎。当然,这种个别的特例不应该成为艺术家忽视深入群众生活,拒绝学习传统艺术的借口。
交响诗篇《雅鲁藏布》是著名电子音乐作曲家张小夫的作品。作曲家的意图是通过音乐体现藏族的母亲河-雅鲁藏布江所孕育的民族文化,体现雅鲁藏布江所哺育的儿女们的生活与感情。在这首作品中作者运用了三种元素:信息时代产生的电子音乐、工业时代产生的管弦乐和农牧业时代产生的民间传统音乐(人声原唱)。这三种极富表现力的元素,被作曲家巧妙地结合成为艺术整体。电子音乐担任乐曲的前奏,引出表现雪域高原的音乐背景,并从剧场后座方向隐隐传来雅鲁藏布江畔的牛皮船歌,在延续的电子音乐背景中,在舞台上出现了三位来自高原的藏族民间歌手,令人难以忘怀的藏北牧歌和原汁原味的牧区盛装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听觉和视觉的冲击。乐曲的中段是根据牛皮船歌和阿里鼓乐素材发展而成的高潮部分,全部由交响乐队担任。当乐队音响达到最高点时,电子音乐模拟的藏族大法号轰鸣而出,与管弦乐交响。高潮之后,作曲家在乐曲的再现部分,不但再次让听众欣赏到动人的牧歌,而且利用电子音乐的特长,做出纵跨整个剧场空间遥相呼应的的男女声对唱,使听众有身历其境之感。从作曲技法和创作元素来看,这首作品可以说是最传统与最现代的结合;从现场听众的热烈反应来看,它是一首雅俗共赏的成功之作。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台来自雪域高原献给新世纪的成功的音乐会。我们要特别感谢来自雪域高原的三位歌手,他们把家乡的牧歌带到遥远的首都北京,带给我们如此美妙的享受。央金卓玛、尼玛次仁和洛桑的歌声将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记忆。
我们期待着更多少数民族作曲家的优秀作品展现在首都舞台上。
注:本文作者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