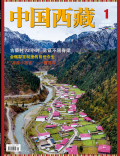拉萨河两岸,风景如画。 戴明摄

清澈的拉萨河水,戴明摄

拉萨河水流进村庄。 周英摄

拉萨渡口的牛皮船。 张超音摄

拉萨的沿河大道。索穷摄
萨河是蓝色的。
四十年前的一个晴和的秋日,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拉萨的我放下简单的行装,便急不可待地去看拉萨河了。
我看见她那松耳石般的蓝色雪浪花,从云山雪谷奔涌而来,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片永生难忘、挥之不去的蔚蓝。
她比我家乡的湘江和洞庭湖还要蓝,她比我后来看到的多瑙河和莱茵河还要蓝,她蓝得那样晶莹,那样剔透,那样纯粹,像一匹刚刚抖开的蓝缎子,像满河跳荡不息的蓝色水晶,像融化了一大片高原深秋的蓝得不能再蓝的天空。
于是,我向这条蓝色的圣河顶礼致敬,用她清凉的雪水洗涤我身上的尘灰和整个的灵魂。
其实,在这以前,我对拉萨和拉萨河心仪已久,我努力搜寻和阅读相关的历史文化、传说、故事和歌谣。田汉先生在话剧《文成公主》中用“红山矗立,碧水中流”来描绘这里风光地势,我觉得是最贴切和精当。
从此,我在拉萨河边这座古城居留下来,长达25年之久,渐渐融入她深厚的文化积淀,感染她浓郁的民俗风情,在这里学习语言,适应生活,成了这个城市居民中颇为活跃和相当积极的一员。白天,我奔走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出入各种各样的人物之家,夜晚,我枕着拉萨河的涛声入睡,做着种种关于自己人生事业和前程的蓝色梦。在那些政治运动不断,“左”的思潮严重的年月,每当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生活上、感情上受到伤害的时候,我总是要跑到拉萨河边、久久的在河边散步或伫立,把满腔的心思向这条蓝色的河倾诉。
从此,我对拉萨河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亲近了。
那时侯,我每年都要用很多的时间和演员们一起,去到拉萨河的上游和下游,农村和牧区,城镇和村寨巡回演出,学习民间艺术,深入生活。我们骑着走马和牦牛,从一条河谷到另一条河谷,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在熊熊的篝火周围,通宵达旦的歌舞狂欢,住农民的泥土小屋、牧民的牛毛帐篷,喝清冽的青稞酒,浓酽的酥油茶,烤芳香的牛粪火,在羊皮口袋里抓糌粑,听老人们讲述拉萨河两岸的故事,传说和种种往事,总是让我们感叹嘘唏,难以忘怀。
拉萨河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主峰,在林周县的旁多峡谷与桑丹岗桑雪山上流下来的热振河汇合,在墨竹工卡县的宗雪城堡前面,与拉里神山上流下来的雪绒河汇合;在墨竹工卡县的嘎采古庙前面,与工布巴拉雪山上流下的墨竹河汇合。就此形成了拉萨河的干流,洋洋洒洒,浩浩荡荡,直泻奔流150公里,最后在曲水县朗钦日苏象鼻湾和雅鲁藏布江合流,形成了雄伟壮观的蓝白相汇的高原奇观。
念青唐古拉山,是雪域高原四大神山之一,传说山上住着威力无边的唐拉雅秀雪山神,他负责保护整个拉萨河谷和布达拉宫,还说他常常穿着白色羊皮大氅,骑着白马,在高山和峡谷之间纵横驰骋,任意游荡。而桑丹岗桑雪山又是岗瓦桑波山神的冰雪城堡,它日以继夜地守护着藏北草原通往拉萨河谷的黄金通道。神山雪水流进拉萨河,拉萨河成了神河、圣河、药水河。老人们说:拉萨河水有八种功德;一甘、二凉、三软、四轻、五净、六香、七饮时不损喉、八喝过不伤胃,消除杂念,净化心灵,健康体肤,掬饮一捧,是人生一大造化。每年藏历八月,拉萨河南岸宝瓶山顶,天空弃山星升起,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纷纷跳进拉萨河清波夜浴,这就是中外游客争相一睹为快的沐浴节。
拉萨河也有航运之利,航运主要靠牛皮船,这种航运工具,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已经出现在西藏高原的河流和湖泊上,它是用柳条支撑牦牛皮制成的,具有很强的柔韧性,不怕礁石和险滩,一只船大约能运载400公斤左右的人畜和货物,船夫们往往从墨竹工卡起行,经过达孜县的德庆镇、拉萨城和曲水县的聂塘镇,大约三天时间,到达雅鲁藏布江的汇合口,从这里再转下山南的贡噶桑耶泽当等城镇。牛皮船只能日行,不能夜行,夜晚将船撑在河滩上,船夫们围着一堆火野餐,在月光下唱歌跳舞,讲故事。这种船只能顺水而下,不能逆水行舟,返程时船夫们就把牛皮船晾干,背着翻山越岭回到拉萨河的上游,一只船大约六十公斤左右,船夫的被子和食物由一只老绵羊驮着,和他相依相伴走过艰难的路程,羊铃叮叮当当的响声,也能消除一些旅途的孤单和寂寞。
拉萨河上有不少渡口,夏天用牛皮船摆渡,到冬春季节,就改用码头木船,还有多座铁索桥,最著名的要算拉萨铁索桥,这座桥是公元15世纪前期,西藏著名高僧唐东杰布,在当地柳梧宗城堡的女长官格桑的支持下修成的,这是当时轰动整个拉萨和西藏的一件大事,也是这位被尊为铁索桥活佛修建的第一座铁索桥,直到现在,桥墩还遗留在拉萨河南岸的乃东香卡村下面。从墨竹工卡往上还有唐家铁索桥,宗雪铁索桥,旁多铁索桥等,这些桥,我进藏以后还看到它们在继续使用,保存相当完好,并且不止一次路过,是当地的主要交通要道。这些桥一般是用6到8根铁索横架河面,中间用兽皮和牛皮,再铺上木板,走起来摇摇晃晃,再加上桥下河水奔腾湍急,响声如雷,让人头晕目眩,胆战心惊。
公元7世纪前西藏高原上的文明史,就像隔着浓云迷雾看天上的星星那样朦胧,人们知道的只有山南的雅隆文明和岗底斯山周围的象雄文明,拉萨河谷的文明,好像是一片空白。其实,拉萨河谷的先民们早在这一带的山丘和河谷,进行农、牧、渔、猎,挖掘洞穴,建造民居,制造了精美的陶器和各种生产生活用品。20世纪80年代,在拉萨北郊娘热乡挖掘出土的曲贡遗址,就提供了生动丰富的例证,那时统治拉萨河谷周围地区的苏毗部落联盟和雅隆部落联盟,同象雄部落联盟一样,是西藏高原上最强大的地方势力。
据藏文古史记载,公元7世纪以前的西藏高原分布着40个或者20个较小的邦国,据我们所知,拉萨河谷就有三四个之多,现在林周县的澎波地方,当时有个叫松波杰·达甲沃的王国,国王住在名叫辗噶尔的城堡,他有家臣年氏和噶尔氏。藏王松赞干布手下的大相,到长安迎娶文成公主的使者禄东赞就是噶尔家族的传人。现在墨竹工卡县直贡地区,当时有个名叫森波杰·赤邦松的王国,国王住在宇拉城堡,现在曲水县江乡一带,当时有个名叫吉若·江俄的小国,国王叫吉杰·芒波,家臣谢乌氏和索氏国王城堡的废墟,我进藏以后还看到过。
公元6世纪末,山南雅隆部落第三十一代赞普朗日松赞和森波杰·赤邦手下的娘氏、巴氏、蔡邦氏等四个很有势力的家族秘密结盟,推翻了森波杰的统治,从而把势力扩展到了整个拉萨河地区,为日后建立吐蕃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拉萨河中游的甲玛沟修建了一座名叫强巴林久的行宫,在这里指挥和策划政治、军事行动,他的妃子在这里生下了西藏一代英主松赞干布。
公元7世纪初,藏王松赞干布建立了西藏高原有史以来第一个统一政权——吐蕃王朝,并且在拉萨河的下游吉雪沃塘,修筑了吐蕃王都拉萨城,迎娶了大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赤尊公主,同时在拉萨红山顶上,建筑了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又在沃唐湖上建造了藏传佛教的信仰中心大昭寺,从那时到现在,拉萨一直是整个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藏王松赞干布把整个西藏分为四大区域,拉萨地区被称为卫如及中区,也就是吐蕃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区。那时松赞干布把西藏分为六十个千户,据我所知,拉萨河流域就有四个千户,即拉萨河上游的吉堆千户,拉萨河下游的吉麦千户,堆隆河流域的玛千户,直贡地区的秀察千户。藏王松赞干布平时和汉妃文成公主、尼妃赤尊公主住在拉萨,夏天往往到拉萨河的上游澎波和墨竹地区等地去度夏或会盟。据说,松赞干布是公元650年,在澎波地区色木岗光明宫殿去世。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内部斗争非常激烈,先是藏王热巴坚在墨竹工卡的强巴宫被反佛大臣杀害,接着藏王朗达玛推行剿灭佛法,捣毁寺院,迫害僧侣的严厉措施,又被佛教僧侣刺杀。朗达玛死后,留下了两个王子维松和云丹,各自拥立一个王子,相互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内战。云丹占领拉萨河谷,这里以牧业为主,居民吃肉较多,所以叫吃肉派;维松退守山南地区,这里的居民以吃糌粑为主,称为吃糌粑派。后人把这场战争称为吃肉派与吃糌粑派的战争,可见,公元9世纪前后,拉萨河谷的牧业是非常兴盛的。
接下来,随着平民起义,豪强争霸,军阀割据,西藏高原进入长达300年的分裂割据时期,佛教经过近百年的沉寂以后,又在西藏的北部青海和西边的阿里重新兴盛起来,他们争相向拉萨河流域传播,以鲁梅为首的卫藏10个青年在青海丹底寺得到贡巴饶赛大师真传之后,在拉萨河上游达孜县境内修建了拉姆切寺,在林周县境内修建了杰乃康寺,在堆隆河边修建热噶寺,他的弟子们进驻拉萨大昭寺,形成4个势均力敌的僧团,弘法传教,兴盛一时。最后,为了争夺土地属民和寺庙的财产,打得你死我活。
南亚高僧阿底峡大师被古格王迎请到阿里托林寺讲经说法3年,接着又到拉萨西南的聂当地方收徒传法著书立说9年,最后在这里圆寂。他是藏传佛教后宏期当之无愧的祖师。他的弟子仲敦巴在当雄豪富昌卡琼瓦等支持下,在拉萨河上游修建了热振寺,成为藏传佛教噶当派的祖庭。由玛尔巴、米拉热巴开创的白教噶举派,也把势力转移到了拉萨河谷,这个教派称为四大派,八小派,楚布噶举派,蔡巴噶举派、竹巴噶举派、直贡噶举派,达隆噶举派,叶巴噶举派等六个教派,主寺都建立在拉萨周围地区。至于从清朝以来,藏传佛教的主流派格鲁派,完全是以拉萨河谷为基地建立起来的。东郊的甘丹寺,西郊的哲蚌寺、北郊的色拉寺,被称为格鲁派的三大支柱,三座道场。这些寺庙,规模特别雄伟,建筑特别壮观,它们依山而建,碉楼高耸,金顶辉煌,如同一座座戒备森严的堡垒群,有着明显的军事防御作用。寺庙僧人少则上千,多则近万,平时在寺庙修行事佛,遇到教派冲突或者战争,他们又是被武装起来的僧兵。
公元13世纪中叶,西藏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噶坚赞和八思巴适应时代的潮流,代表了藏族人民的愿望,归顺了大元王朝,使西藏从此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整个西藏分为13个万户,拉萨河上游属于直贡万户和甲玛万户,下游属于蔡邦万户。公元14世纪中叶,乃东万户长强曲坚赞推翻了萨迦王朝,建立了新兴的帕竹王朝,他在西藏各地建立了17个相当于县级行政机构——宗(城堡),现在达孜县境内的扎嘎宗和堆龙德庆的柳梧宗,曾经在历史上盛极一时,势力特别强大,每个宗都有一座建立在山头岩峰上的坚固城堡,有的至今还有遗迹和废墟可寻。公元17世纪以拉萨为基地的格鲁派势力,消灭了首府设在日喀则的藏巴汗政权,建立了甘丹颇章王朝,得到清朝中央强有力支持和援助,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交往日渐频繁。当时拉萨有两条官道,直接通往北京,一条是沿着拉萨河东行,经过蔡公塘、达孜、墨竹工卡,翻越贡布巴拉雪山,取道昌都、四川进京。一条是由沿拉萨河北上,经过澎波旁多热振,取道藏北、青海进京。当时有许多的大臣、官吏、官兵经由这两条路,到拉萨和西藏各地,其中不少颇具文才的人写下了许多诗歌和游记,记下了他们亲眼所见,亲身所感,亲耳所闻,其中有不少文字记述了拉萨河谷的风光景物,使我们今天读起来还是倍感亲切,耳目一新。
例如,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清朝官员焦应旗所写的《藏程纪略》一书中记述了他押运粮草,从西宁随大军进藏所看到的拉萨河谷的情形,中间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迨观藏内形胜,山水环秀,土田沃衍,树木浓荫,民居稠密,且风和日暖,严冬之际,冰雪不凝,洵塞域之别有天地也。平川中拥一石山,较诸风独小,上建寺院,为活佛所居,层楼翠阁,几数百重,金光绚丽,美不胜述。
还有雍正十年,(公元1733年),清朝官员山东知州王世睿,由四川到拉萨公务,历时9个月,他用非常优美形象的文字,描写了沿途风光景物。例如,他是这样描写拉萨河中游的重镇墨竹工卡的:
墨竹工卡疆域褊小,而陵谷开敞,两山列峙,屈曲随人,蛮寨蛮寺,若绘若画,其淡远浮动之势,浑如仙岛。且人勤耕稼,稻畦乡错,一如内地,溪流清浅中之鼓鬣而浮潜上下者,殊有游泳自得之乐……
公元1961年到现在时光又过了40年,这也是拉萨河谷变化最大的40年,现在,拉萨已成为一座传统和现代化相结合的旅游城,拉萨河两岸的田野和村庄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洁白美丽的新村和各种造型美观的藏式新楼不停的从柳林和陵谷中显现。
我祝愿这条圣河越来越美好,两岸的居民越来越富裕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