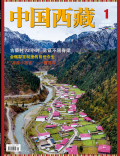科加寺是阿里地区最大的寺庙,已有1000多年历史,来这里朝圣的大都是阿里地区和尼泊尔的信徒。
在阿里象雄文化发展协会的安排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编导赵忠义先生的全程资助下,我有幸进行这次难忘的象雄文化探索之旅,行程自冈仁波齐下的达钦寺到科加寺—甲尼玛列石阵—穹隆欧卡尔遗址—古格故城—托林寺—阿如的古代石屋—罗波的古人类墓地,最后到措勤,走遍阿里七县一镇,历时16天,体验了阿里的风土人情和象雄文明的深厚底蕴。
在科加呆了4天,从燠热的普兰谷地上到气候凉爽的巴噶草原,海拔提升800米,戈壁的清风吹来,每个人都觉得神清气爽。
我们今天的行程是从甲尼玛到穹隆欧卡尔遗址参观考察。沿途土丘平缓,艳阳高照,冈仁波齐和拉昂措的风光一路相伴,到处是茂盛的“扎麻”——毛刺植物和成群的野生动物,视野开阔。
举办象雄文化遗址摄影展。
就在大家最不经意的时候,考察的第一个目的地——甲尼玛列石阵已经赫然在目。
甲尼玛列石群(石碑)位于阿里普兰县境内拉昂湖以西约20公里一个叫甲尼玛的开阔地上,我们共发现两座石碑遗址,当地牧民称它们为“达热”石碑和“仁钦曲顶”石碑,两座石碑相距1公里,东边的有6根石柱,最高的达2米多,被路人挂上哈达,西边的石柱少些。在这方圆几十公里内都没有石材的戈壁滩上这些孤傲的立石显得突兀而奇特。当地藏族牧民称这种石碑为“斯贝多仁”——宇宙之碑。其实,“斯贝”在藏文中有非常远古的意思……当然,今天已经没有人能说清这些石碑是何年何月因为什么缘故立在这里的,它就像大地上的行为艺术,令人猜测和冥想。
既然连当地人都无法理解其中的缘由,且听学者们是怎么说的。西藏社科院的顿珠拉杰说,根据我个人的实地调查,发现这类石碑遗迹遍布整个西藏西部和北部高原。根据顿珠啦正在翻译的苯教经卷《札巴岭扎》记载:“……当时(第二代藏王牟尼赞普在位时,约公元1世纪),在西藏腹地修建了37座苯教师集聚点、37座佛塔、37根水晶石碑和37座墓葬”。这一段描述说明,立白石碑(“白”是指无字碑)的风俗早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已在西藏高原盛行,而且这些石碑与寺庙、佛塔和墓葬有着密切的联系。
至于说到这些石碑的作用,意大利藏学家约瑟夫·杜齐将其简单说成是“巨石阵”。他猜测:“它们是陵墓还是出于某种目的作为区分区域的标志?或许兼而有之?!”而另一位外国学者约翰·布赖查则认为,这种石碑除了墓葬以外还不应该排除另一种功能,那就是“本部落首领、牧师或其他本部族内有威望的人物去世后,为他们而立的纪念碑”。其它还有一种功能就是立盟誓碑,这种传统一直到吐蕃盛行时期还在保留,这一点不难从拉萨现存的吐蕃时期的石碑中可以看出。
嘎加琼珠活佛,1949年摄于阿里。
其实,“白”石碑跟古墓葬遗迹一样,是西藏西部和北部高原上曾经盛行一时的前佛教文化现象,是象雄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告别了甲尼玛,我们于下午3:45分到达著名的穹隆欧卡遗址。一般认为这是象雄王国最后的首都和政治中心。遗址建在一个孤立的山头,巨大的城门正对着南方的河谷,50年前还能看到石砌的城门台阶现已被坍塌的砂土掩埋。城门上方的山上有个“增钦”——古代的蓄水池,圆形,面积约200平方米,水池底部有铺设石板的痕迹,当地的门士四村村长次旺认为当时此处也许有水源,也许降水比较丰富,水池里的水可能用作建设,也可能用于生活,至少说明当时的气候条件比现在好。在遗址中部的山坡上,发现大量建筑遗址,其中有糟朽的木构件、灶灰等。几年前这里出土一件金属双面佛像,被文物部门精心收藏……总之,穹隆遗址的丰富、宏大和久远的历史信息给了我们深深的震撼。
从穹隆城堡下来,我们直奔山下位于穹隆河谷北侧的秋那古墓葬群。这里海拔4360~4390米,是一个大型古墓葬群遗址,共有300座墓葬,最大的面积为400平方米,最小的为5平方米,总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还有一座墓上立有白石碑,其中只有两块仍然立着,5块小石碑已坍塌在墓地上。这些墓葬的形制一般为方形,均用石块砌框而成。其中有的墓葬形态独特,里外两层(外面一层是圆的,里面一层是方的),当地人称这些墓葬为“门突儿”或“杂崩”(砾石堆)。
“门突儿”,一般译作“门人墓”、“门巴人的墓葬场”,在西藏西北部地区多有发现。至于说到何为“门巴人”,则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藏学家东嘎·洛桑赤烈在其藏学辞典中写道:“门域,指大部分门巴人居住地。在藏文史籍中有各种记载,有的把藏尼边境的部分地区的(人)称为门巴,而有时把不丹也称为门巴。无论怎样,藏王松赞干布之父郎汝·松赞被门巴剧毒所害之说中的‘门巴’究竟指哪个地方的人值得研究”。从以上这些观点分析,历史上的门巴随着时代的不同,其疆域和民族有很大的区别。
曾经亲自到过这里考察的顿珠拉杰说,根据大量的实地调查表明,当地人一般认为“门”是一种古老的民族,这个民族曾居住在现在的西藏西北部地区,信奉一种不是佛教的宗教,人死后要埋葬。所以,目前在广袤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所遗存的古墓葬都被认为是“门”族留下来的,只是其历史太久远,人们记不清具体的实情,所以笼统地称它们为“门突儿”。
阿里首届藏医培训班结业,中排右起第六为阁龙·丹增旺扎
而当地的学者则说,既然“门人”信奉不是佛教的宗教,人死后要埋葬,从文化特征上看那应该是象雄时期的苯教徒。(因为)藏族土葬风俗的长期流行,是与藏区早期苯教盛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萨迦派的扎巴坚参在其所著《王统世系》中,根据最古老的文献资料描述了苯教早期传入西藏的情形。他指出苯教或其更早的宗教形态“突儿本”(墓本)是在止贡赞普死时传入的。这种宗教仪式来自象雄和吉尔吉特。
究其原因,帕·克瓦尔耐指出:“完全是因为辛和苯波精通丧葬仪式才把他们从象雄和勃律(吉尔吉特)请到西藏来的……止贡赞普……死后尸体留在了地上。从象雄召来了苯波,让他们修建陵墓并第一个举行相应的葬仪”。只是由于“苯教的衰落导致了土葬习俗的衰落。869年爆发了一场席卷吐蕃全境的平民和奴隶大暴动,暴动的民众于877年将吐蕃王室陵墓挖掘一空,流行了长达几千年的土葬风俗也从此崩溃。”这些学者的论述给了我们解开“门突儿”之谜的一些线索。其实,我们不但对古老的象雄文化知之不多,对有关阿里文化的一些常识不见得就理解准确。
阁龙·丹增旺扎(中)及他的弟子
譬如关于“阿里廓尔松”,多译作“阿里三围”,一般指布让“雪围”,古格“崖围”,芒域“湖围”。然而,阿里当地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本教高僧阁龙·丹增旺扎在《阿里历史宝典》中写道:“(‘阿里三部’只是行政区域的称呼)……假如当时吉德尼玛滚(在占领阿里时他)有两个或四个孩子,(他)将阿里的地盘分封给这些孩子,那么如今的(阿里)将会是阿里二部、阿里四部(这样的概念)”,并不是现在一些人据说的“三围”。
查《藏汉大辞典》,藏文“廓”字解释为“②方域,地区:东北区。大陆地带。阿里三区等”。据《安多政教史》记载,阿里三部由布让、芒域、桑嘎、黎、勃律、象雄和上下赤岱组成。也许我们对“阿里三围”的理解真的有错?
有些汉文著作将冈仁布齐、玛旁雍措湖、拉昂色措湖描写为“神山”、“圣湖”、“鬼湖”等。而在藏文典籍中只有“腊日腊措”——魂山魂湖这样的描述,并没有所谓“神湖”、“鬼湖”的提法。当地人说“玛旁”与“拉昂”均为象雄语,是古代两个“玛姆”的名字,她们分别掌控着“拉昂措”和“玛旁措”,称作“拉昂色措”(金湖)和“玛旁雍措”(玉湖),其地位是相等的,从来没有所谓“神湖”和“鬼湖”之分。
协会工作人员向群众赠送象雄文化丛书
我们在阿里采访时,当地举办“象雄文化遗址摄影展”,展览醒目的位置上挂出一张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图片。主办方说,我们的先人对遥远的大峡谷地区很早就有了解和描述,将其称作“工昌荣”,“工”指工布,“昌”为隘口,“荣”则是指峡谷。
这让我想起藏族学者更敦群培对“雪域”这一基本概念的考证,他曾说:“人们将喜马拉雅山和西玛班达等译为‘雪域(具雪)’。但是,所谓雪域并非仅指雪山,因为它已成为整个印度北部山脉的成千座雪山、林山和草山的习惯总称。如《正法念处经》一书所载:‘历史上,此山名为山中尊雪山,许多雪峰高达上千由旬,被柏树、檀香树和多磨罗树等装点,蔚为壮观。’由此可见,雪域山上生长着林木。《迎请尊者》一书中‘亦有雪域的特征之一是该处长着松树,牦牛蹄子踩碎了石块’等记载。再看看印度以雪域为题材的诗歌,很多都是描写雪域境内的森林、鲜花盛开的草原和牦牛的。所以说,被雪域的名称所迷惑,认为雪域山区的一切均生存于冰雪之中的观点,与认为萨迦的一切生存于灰色泥土当中的观点毫无二致。同样,‘雪域山上生长着各种药草’一句,亦指那里的草山和林山上长着各种药草。”从地理学的角度认识“雪域”,纠正了人们对“雪域”的误解。
类似的很多例子使我们觉得作为藏文化的传播者,应该从包括象雄文明在内的藏族传统文化中认真谦虚的汲取养份,而不要再自以为是地犯这种对基本常识的文化“误读”才好。这也是我们这次阿里之行的一个收获吧,实在是不虚此行。